医院的女战士
中科让您告别白癜风秀健康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4267800.html
医院的女战士
她医院
王海会15岁时在家乡四川达县浦家乡参加了红军,分配到红三十军政治部宣传队,投入了革命的浩荡洪流之中。年从各军宣传队抽人到通江培训一个月,她经过培训分医院当护士。当时,总医院院长是周光坦,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护士学校校长苏井观,医务主任周吉安,看护长林成芬,她的班长是徐明秀。年初,总医院离开王坪,经过崇花县时,留下红医院。医院担任护士长,由于出色的工作,她被吸收入党。医院在崇花县待了约半年,9月份随返回来的红四方面军第二次过草地、爬雪山,经毛儿盖、懋功等地向川康边界的天荃、芦山一带进军,遭到四川军阀刘湘军队的阻截。年8月又第三次越过茫茫草地,秋天到甘肃会宁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靖远渡过黄河,总医院进行改编。大部分人调走了,医院。部队进入祁连山后,医院政委将她们的枪支、子弹集中起来交给那些身强力壮的男同志,一部分不能用的枪支埋了起来。党团员把党证团证、重要文件也埋了。由于长期缺乏粮食、食油和盐,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坏,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了。那是一个阴冷的日子,她们下山找粮食,正和老乡换黄米时,被马家的地方民团包围。尽管她们用仅有的几支枪奋勇突围,但寡不敌众,终于被俘。和医院的邢之秀、申天任、姚芝珍等,还有红九军敌工部副部长吴仲廉。敌人将她们押送张掖,医院许多同志关在这里,还见到张琴秋、陶万荣。在向西宁押送途中,王海会亲眼看见敌人对红军战士血腥屠杀。她一直和张琴秋、吴仲廉、陈万珍、赵玉香等在一起。张琴秋在张掖时就化了装,头上包了块破布,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化名苟秀英。张琴秋两只脚上打了许多血泡,行走很困难。她们几个人轮流扶着张琴秋走,乘敌人不注意,把她塞进拉粮的大车里,用毡篷布盖起来。敌人将她们关押在羊毛厂做苦工,每天拣羊毛,用烂皮子熬胶等。不多久,张琴秋被敌人提出去煮饭。张琴秋临走前,还来看望大家,鼓励大家要坚持斗争,不要忘了党、忘了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马家军将她们名义上释放,实际上是给其部下分配做老婆,做佣人。王海会躲在茅屋里,后来溜了出去,医院找着一个姓窘的女外科大夫。窘是平时看病相识的,对她们的遭遇很同情。在窘大夫的帮助下,她被介绍去一个当时在盐局里当文书的人家里做佣人。年6月文书全家回西安老家,又把她介绍给同院一个商人陈宝家做佣人。她在陈家待了三年,在忧心忡忡中被迫做了二房。全国即将解放时,马家军拼命抓兵,陈家无法应付,铺子顶了壮丁,就此倒闭。青海解放的喜讯踏着轻快的脚步走来,呼唤起她心中久已沉睡的热情。一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将她们这些流落红军召集在一起,亲自接见,勉励大家发扬革命精神,协助政府工作。她被安排在青海省军管会里帮助搞肃清反革命工作,收缴马家军流散下来的枪支、弹药。和她一起参加肃反工作的女红军还有谢青英、王淑惠等。西宁市成立市政府,肃反工作告一段落,她们被分配在街道上做居民工作。人生如流,岁月如流。她一直在基层岗位上兢兢业业,努力工作。
历经磨难而没有死的“共产丫头"当兵就要当红军,
处处工农来欢迎,
穷人参军为革命,
红军打仗为穷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
打倒土豪和劣绅,
人人都把田地分,
军属田地有代耕。
……
这歌谣是红军女战士安明秀唱的许多红军歌谣中的一首。这些歌曾伴随红军西征的步伐,把革命的火种撒到河西走廊,撒到黄土高原!半个世纪过去了,那缭绕在祁连山顶的悠悠歌声呢?那遗留在河西走廊的泪滴和火光呢?安明秀在家乡四川省阆中县参加红军,当时才13岁。她的两个哥哥也参加了红军,幺爸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两个哥哥在过草地时先后牺牲,幺爸一直没有下落。她参加红军时年龄小,又爱唱爱跳,被分配到总部文工团,医院当看护。西路军时期,医院。部队从倪家营子突围时,她背个小包袱,拉着马尾巴……噢,祁连,你高峻、严酷,在你脚下埋藏着一个个失败者的故事。部队从梨园口进入祁连山。总医院的几位领导商量,要把安明秀这些小女孩带出去,找个可靠人家安顿下来。领导把大人分成几批,一批五六个人,由一位领导带领。李传珠负责安明秀几个人。她们在山里周旋,常常是已经分手的同志,过不久又碰上了,然后再分头出奔。那时没有带伤员,伤员在永昌、山丹丢掉一部分,在倪家营子丢掉一部分。她们不敢到伤员跟前去,去了伤员死死拉住不放,好像要把肉拉下来,哭着求着叫带上他们,可是谁又能带动伤员呢?暮色中几颗稀寥的星星泛着惨淡的白光,寒冷夹带着腥味的风掠过山谷。远远走来一个牧羊人,背着背篓,拄着棍子,对她们谎说:“这里僻静,附近没有马家队伍,就在这里过夜,等天亮了再走!”带领她们几人的李传珠安置大家歇息,自己也在林边躺下。她们哪里知道,四周竟是马家队伍的营地。“砰,砰……”枪声撕碎周围的冷寂。天刚亮,马家骑兵冲下山来。李传珠闻讯喊道:“快钻树林子!”随即和一位男同志滚进身旁林棵之中。安明秀等几个女孩跑得慢,被抓获。马家兵搜出余碧秀身上带着的三个马尾手榴弹,看了看,瞧不起地说:“你们拿上这烂东西有啥用?”说罢扔到山沟里去了,又说,“别怕,女的我们不杀!”一片粗犷的群山,一望无垠的白雪,山路就于其间蛇一般弯去,深深地战栗着,战栗着。石崖下,路边上,都是枪杀、刀砍、饿死、冻死的红军尸体,看不成啊!苍莽大地沉没进夜霭的阴影中,唯有祁连之巅,在晚祷般仰着的群峦之上,幻成一个黑色的梦。她们被带到一个山沟里蹴下,山旮旯有几户老百姓。马家兵把她们圈在一个大屋里,地上铺了些草,用黑碗碗送来点面糊糊。有人喝了点,有人没有动。安明秀至今见山就心烦,就反胃。有人叫她浪山去,她就说:“早就浪够了!”她们被一站一站地押到青海,押到西宁。从小桥到西门,路两边都围着白布,他们从布中间走过。后来听说,那是马步芳欢迎他的队伍用的,她们去时还没撤掉。她们被圈在马步芳军部的大院里站着。马家兵押来早先被俘的女红军说:“你们认识这些新俘虏吗?认识的就领上走!”有人被领医院,有人被领到羊毛工厂。安明秀曾在总部文工团待过,新剧团的黄光秀、党文秀等好些人认识她,把她领到了新剧团。新剧团解散时,有人被押往张掖,余下的分配给马家军官做老婆或佣人。安明秀等年龄小的被分配做丫鬟。安明秀到马步芳的财政厅长马××家当丫鬟,从此没有了天真和童稚的欢乐。主人家从来不称呼她的姓名,只叫她“共产丫头”。她劈柴、烧火、打水、洗衣,干些粗重活。她年纪小,干这些活很吃力,常常挨打受气。她天天晚睡早起,常常瞌睡。马家二少爷5岁,从小害小儿麻痹症。安明秀要顿顿压着他的胳膊喂饭,还得白天晚上地抱着,哄他睡觉。她实在困得恍惚得不成,一次把床上的枕头当成了二少爷抱在怀里,一边瞌睡一边哄。马厅长见了,照她就是一马棒。唯有在马家做工一辈子,外号“白头阿奶”的老佣人还关心她,用受苦人“命不好”的信条劝慰她……厅长的大少爷十一二岁,常常穿着仿制的军服,腰间挂把小马刀,在院子里逞威风。一次,大少爷把安明秀叫到院里,大声吆喝着:“立正,稍息,正步走!”安明秀不理会,扭头就走。大少爷截住她,口出脏话,伸手就打。安明秀扇了他几个耳光。他哭着去找他妈——厅长的大老婆告状。大老婆个子尕,安明秀等背后叫她“尕阿妈”。她听儿子说罢,一边骂,一边抄起擀面杖,劈头盖脸打安明秀:“我把你这个贼婊子,还敢打我的尕娃哩!”安明秀顺势抓住大太太手上戴的玉石镯子,把她推倒在案板上。一个丫鬟赶快把“尕阿妈”扶起来,说:“太太啊,尕共产党把你打坏了吗?”安明秀又去打那个丫鬟。大太太气急败坏,一边骂一边退了出去:“你这个该死的共产丫头,吃了豹子胆了,还敢打我?等老爷回来有你的好的,等着吧!”其时,厅长回河州娶三老婆去了。听说厅长就要回西宁,安明秀跑了。她一口气登上西宁市的南山,朝山里走去。面对开着野花的乱草岗子,她彳亍独行,能到哪里去呢?安明秀跑到绽永贵家。绽永贵是马步芳的参谋,是土木建筑工程师,会吹口琴,常去剧团伴奏。绽永贵家有安明秀的一个四川老乡,叫祁明杰,也是被俘女红军,给绽做二老婆。安明秀在绽家躲了十来天。马步芳把绽叫去训斥:“给你一个女红军了,你要几个?”绽只好让他妈把安明秀送回厅长家。厅长用烧火的铁钳,打得她遍体鳞伤,躺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床。这天,安明秀端着盘子给厅长送饭,厅长正在做礼拜,只好在门外等候。由于过度劳累,她站着站着就打瞌睡,手中托盘上的碗打翻在地。厅长勃然大怒,掏出手枪追了出来。安明秀拼命跑,一只脚迈进厨房的门,可门被铁链子拴住了。她从窄小的门缝中往里挤,枪声响了,她正好挤进厨房。主人家感到这个不听话的“共产丫头”不能要了,打算把她许给传令兵当老婆,可倔强的安明秀就是不同意。“白头阿奶”是从小看下马厅长的,想要安明秀给她当孙子媳妇,安明秀同意了。安明秀和“白头阿奶”的孙子马国英结婚时,厅长的大老婆假模假样地送她一床洋布被子,被里子是横着缝的。按迷信的说法,盖上这种被子,生孩子要横位,要难产。这是盼着她死哩!花开花落,岁月悠悠。安明秀历经磨难没有死,而且人丁兴旺。四个孩子,两儿两女都出落得超俗不凡,其中三人是共产党员。安明秀很为自己的儿女自豪。
失去平衡的记忆
何光明,总是落落寡欢,心的荒野常常升起一缕缕轻烟,还跳动着红色的彩带。红火的灼伤,留下的只能是黑色的伤疤。这是失去平衡的记忆……何光明,四川省通江县人,9岁时父亲病故,妈妈将她给本镇姓唐的一家做了童养媳。13岁那年村上来了红军,还有许多女红军。有个女红军干部叫陶万荣,到她家宣传。她思想通了,还扩大了本镇一个叫钱家华的女孩子一起参加了红军。队伍要出发,妈妈舍不得离开她,把她藏了起来。她偷跑出来,找到红军,医院三分院当护士。她以青春年华投入陌生而有吸引力的战斗生活,每天给伤病员洗伤口、换药。她还参加了新剧团唱歌队,经常在晚上慰问重伤员,给伤员唱《慰问伤病号歌》:苏区硬是好,慰劳伤病号,……红军伤病号,乐得哈哈笑,伤病痛苦都忘掉。重上前线多杀敌,报答姐妹来慰劳。每次开大会之前,她们还登台表演打花鼓、唱歌。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在中岗成立了卫生学校。她被三分院抽出来进卫生学校学习了7个月后仍回到三分院做护士。部队到甘孜,上级把她调到总部卫生所工作。在这里,她和总政治部的李金同结了婚。部队靖远渡河,渡了三个晚上。上边来了命令,剩下的部队停止渡河。何光明与爱人李金同在渡河时分手,她到河西,他留河东。从此,两人被凄厉的秋风和飞卷的浪花隔开。医院,在山丹住了一个多月。马家队伍将山丹团团围住,发生了几次血战。医院要抢救伤员,还要运送弹药等。为了解决部队给养,上级把会骑马的五六十名战士组织起来去调粮。何光明参加了第二次到大佛寺的调粮,在半山坡碰上马家军,队伍被打散。她在大佛寺一带右腿负伤,和战友吴清香、李树珍一起回山丹找部队,夜里住在老乡家里被马家兵搜捕。敌人先是把她们放在马家军孟营长家当仆人,伺候营长太太,以后又把几个难友分配给老兵做老婆。何光明在孟家待了四个多月,被逼迫与马家军中的阿訇杨德清结了婚。她逃跑,被抓回来毒打;她喝碱水,想以死抗争,又被救活。她没有屈服,寻找机会再次逃跑出来,逃到拉骆驼的吴义贞家里,与吴结了婚。她总是落落寡欢,怀着失去平衡的记忆,在不可知的命运中,宿命般度过自己莫测的一生。连载八十七
《西路军?生死档案》冯亚光著编辑:高婉鑫审核:王麟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sohkw.com/wazz/12654.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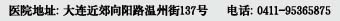
当前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