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芳综论郑笺对诗经中情感诗句的
本文通过追溯“按迹以求性情”一语的历史来源,并在全面考察《诗经·郑笺》的基础上,认为《郑笺》对《诗经》中的情感诗句的阐发,内容丰富,感情饱满,释解恰切,深得风人之旨。而前人谓郑玄“按迹以求性情”时所举诸例,其实郑氏的解释,大多数有其合理性。因此,千余年来评价《郑笺》影响颇大的这一说法,并非事实,有失偏颇。
综论《郑笺》对《诗经》中情感诗句的阐发
--兼驳论《郑笺》“按迹以求性情”说之失实
李林芳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影响后世至深至远。《诗经》中涉及各类情感表达时,或感情真挚,或热烈奔放,或淡雅委婉,或伤痛欲绝,为后世情感类诗所宗。汉人解《诗》,以《毛传》、《郑笺》为最。但对《郑笺》释诗,中古以来谓郑玄擅长《三礼》,以礼释诗,多扞格不通,甚或谓其“按迹以求性情”,转使诗义晦塞。明代竟陵、公安诸家,主张“以五七言之法”解诗,更斥《郑笺》为隔靴骚痒,大失诗旨,近今人之评价郑氏,亦多持此观点。本文在全面考察《诗经》诗篇的基础上,探究《郑笺》阐发与释解《诗经》中情感的方式与特点,以说明《郑笺》对情感的阐发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同时,本文认为前人所谓《郑笺》“按迹以求性情”之说,并非事实,有失偏颇。相反郑氏释诗中情感,多谅人察己,细致入微,曲尽情致,深得风人之旨。
一、对“按迹以求性情”的历史追溯论《郑笺》“按迹以求性情”,最早出于北宋著名文人李清臣语。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云:
郑氏训诗之失。郑氏之学,长于礼而深于经制,至于训诗,乃以经制言之。夫诗,性情也。礼制,迹也。彼以礼训诗,是按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欤。《緑衣》之诗,郑以为“褖”。“不谏亦入”,郑以为入于宗庙。《狼跋》状周公安闲自得于?疑之中,故有“公孙硕肤,赤舄几几”之句,而郑谓之“公逊”。《庭燎》见宣王有怠政之渐,而郑以为设鸡人之官。诸类此者,不可悉举,岂可谓之知诗邪!淇水文[①]。
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亦引之,云:
郑之释繁塞而多失。郑学长于《礼》,以《礼》训《诗》,是案迹而议性情也。“緑衣”,以为禒;“不谏亦入”,以为入宗庙;“庭燎”,以为不设鸡人之官,此类不可悉举[②]。
之后清人胡承珙于《毛诗后笺》中解说《绿衣》一诗时亦简引之:
篇名《绿衣》,从毛为是。此与《内司服》“绿”误为“褖”者不同。郑学深于《三礼》,往往以《礼》笺《诗》,所谓“按迹而议性情”者,以此[③]。
清人胡培翚《研六室文钞》中亦引及胡承珙的话而稍有变化,云:
郑学长于征实短于会虚。前人谓其“按迹而语性情”者以此[④]。
后世亦有对这句话提出反对意见的,如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云:
(王应麟)至采及李氏说,诋《郑笺》繁塞,而其失愈多。“郑长礼学,以礼训诗,是按迹而议性情”,如此妄说,取之奚为?其于本原之地,未曾究通,则博雅乃皮毛耳。葢南宋道学方炽,无人能读古书,厚斋亦限于时风众势,一齐众咻,遂至茫无定见[⑤]。
此种反对,亦只是捍卫门户之言:对于批评《郑笺》之观点一概驳斥,而未具体说明为什么“按迹而议性情”不对。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自宋至清认为郑玄解《诗》是“按迹以求性情”者大有人在。与古人相比,今人亦有持类似观点者。最有代表性的如洪湛侯先生《诗经学史》中说:“徒事礼仪、礼制之烦琐考证,忽略诗篇之文学感兴,舍本逐末,自不可取;然而诗中涉及之名物制度,不循《礼》而无法索解者,则仍须读《礼》沟通,自不得视习《礼》为余事。”[⑥]认为《诗》中涉及名物制度,郑玄以礼解《诗》是必不可少的;但以礼笺《诗》却又忽略了《诗》的文学性。
不过,也有部分学者逐渐注意到《郑笺》不仅仅是“案迹”而已,亦有阐发《诗》中情感之处。如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⑦]、沈薇薇《郑玄〈诗经〉学研究》[⑧]、李世萍《郑玄毛诗笺研究》[⑨]中都进行了相关论述,并对《郑笺》阐发情感的方式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但这些文章或是举例性质的说明,或是从文学角度进行的探究,或未深入考察郑玄阐发情感的特点,而仅是面上的概括。所以本文将在全面考察《诗经》所有诗篇的基础上,探究《郑笺》阐发《诗经》中情感的方式,讨论《郑笺》阐发情感的特点,并对自宋以来有广泛影响的“按迹以求性情”的说法加以驳斥。下面且从郑氏对《诗经》中情感的阐发谈起。
二、《郑笺》阐发情感的方法郑玄在笺诗时,其实是非常注重阐发诗中之情的,或明白显豁,或委曲宛转。下面将分八例分类说明之。
(一)直接点明诗中情感例即《郑笺》用一句话明白地表示诗句(或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据情感所涉对象的不同,又可分为八类。
对君
君即国君,亦可指凡在上位的统治者。如点明对统治者的痛恨:
《墉风·黍离》:“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笺》:“此亡国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
《郑笺》以“疾之甚”一语,直接点明诗句中对于亡国之君的痛恨之情,感情强烈,干净明了。
又如对统治者的哀伤:
《小雅·頍弁》:“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笺》:“刺幽王将亡,哀之也。”
《郑笺》以“哀之也”一语,直接点明诗人对于幽王享乐无度而导致国之将亡的深深的哀伤。
又如对统治者的赞美:
《大雅·下武》:“昭兹来许,绳其祖武。”《笺》:“兹,此。来,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进于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践之迹,美其终成之。”
一句“美其终成之”直接点出诗句中对于武王效法先王勤行善道,最终成一代贤君的赞美之情。
2.对臣
臣即国之大臣。如点明贤者对国之贤臣的喜爱:
《墉风·干旄》:“彼姝者子,何以畀之。”《笺》:“心诚爱厚之至。”
又如百姓对贤臣横遭厄运的痛惜:
《秦风·黄鸟》:“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笺》:“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赎之者,人皆百其身。谓一身百死犹为之。惜善人之甚。”
据《小序》,黄鸟乃国人伤痛秦穆公以三良陪葬之诗。《郑笺》以“惜善人之甚”这一句,直接点出了国人对于三良之死的极度痛惜,简洁明白。
又如百姓对贤臣的爱戴:
《豳风·九罭》:“无使我心悲兮。”《笺》:“周公西归,而东都之人心悲,恩德之,爱至深也。”
又如对于佞臣的厌恶与痛恨:
《小雅·正月》:“好言自口,莠言自口。”《笺》:“自,从也。此疾讹言之人,善言从女口出,恶言亦从女口出,女口一尔,善也恶也同出其中。谓其可贱。”
3.对黎民
黎民主要指国家的平民。如对黎民痛苦的哀伤:
《小雅?四月》:“山有蕨薇,隰有杞桋。”《笺》:“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伤之也。”
《疏》:“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残乱,惊扰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诗,以告诉于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悯之也。”一句“伤之也”明确点出了诗人对于黎民苦难的伤痛与怜悯。
4.对父母
如点明诗人不能赡养父母的遗憾、惋惜:
《小雅·蓼莪》:“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笺》:“此言供养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终养。恨之言也。”
5.对丈夫
如点明妻子对丈夫劳于王事、远行在外的疼惜:
《召南·殷其靁》:“何敢违斯,莫敢或遑。”《笺》:“何乎此君子适居此,复去此,转行远从事于王所命之方,无敢或闲暇时。闵其勤劳。”
又如丈夫久役于外,妻子思念丈夫:
《邶风·雄雉》:“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笺》:“日月之行,迭往迭来。今君子独久行役而不来,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辞。”
又如妻子对去世的丈夫的深情重谊:
《唐风·葛生》:“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笺》:“言此者,妇人专一,义之至,情之尽。”
丈夫故去,妻子念之不已,希望自己死后仍与丈夫同居一室,尤可见妻子之于丈夫的深情。郑《笺》此处以“义之至,情之尽”一句,直接点明妻子的情感,而且其中的“至”与“尽”用得非常准确,切实描摹出妻子在丈夫去世后极端悲怆与思念的心理,将妻子的深情展露得淋漓尽致。
6.对妻子
如点明对妻子的极度喜爱之情:
《齐风·鸡鸣》:“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笺》:“虫飞薨薨,东方且明之时。我犹乐与子卧而同梦。言亲爱之无已。”
7.对朋友
如点明对朋友的亲爱之情:
《郑风·女曰鸡鸣》:“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笺》:“宜乎我燕乐宾客而饮酒,与之俱至老。亲爱之言也。”
又如对坏朋友的厌恶:
《小雅·谷风》:“将安将乐,女转弃予。”《笺》:“朋友无大故则不相遗弃。今女以志达而安乐,弃恩忘旧,薄之甚。”
8.其它
如点明对自己境遇的感伤之情:
《小雅·正月》:“念我独兮,忧心殷殷。”《笺》:“此贤者孤特自伤也。”
《郑笺》一句“孤特自伤”直接点出了诗人对自己在小人夹攻、胡作非为情况下的自我感伤之情。其中“孤特”一词,用得非常准确,仿佛郑玄与诗人融合为一,完完全全体会到诗人的品格与在此种境遇下的心境。古人所谓“心知其意”,恐即类此吧。
又如点明对家乡的思念:
《王风·扬之水》:“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笺》:“怀,安也。思乡里处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何月我得归还见之哉?思之甚。”
(二)释因例即说明某种情感产生的原因,而这种感情往往在诗句中是直接体现出来的。采用这种方式,将诗中情感落于实处,使情感更加具体,令读者易于领会。
若从原因所关涉的对象来看,可分为以下五类。
父母
《召南·草虫》:“未见君子,我心伤悲。”《笺》:“维父母思己,故己亦伤悲。”
诗中直接说明女孩子内心的悲伤。为何悲伤呢?《郑笺》中解释:出嫁时,父母思念自己,所以自己内心亦感到悲伤。《疏》中并引《礼记》中语:“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郑笺》之释,使女子的“伤悲”得以具体化,既写出分离之思,又有体恤父母思己之悲,即情即景,柔肠百结,淑女孝子之形象,一下子便活脱脱地展现出来了。
2.丈夫
《小雅·杕杜》:“有杕之杜,其叶萋萋。王事靡盬,我心伤悲。”《笺》:“伤悲者,念其君子于今劳苦。”
女子之所以“伤悲”,是由于其丈夫征戍未还,忧心其丈夫劳苦于外。《郑笺》之释将妻子对丈夫的深情表现得明白显豁。
3.男孩
《郑风·丰》:“悔予不送兮。”《笺》:“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时不送则为异人之色,后不得耦,而思之。”
《疏》:“予当时别为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为留者,亦不得为耦。由此故悔也。”可见这个女孩子之所以后悔,是因为当时没有送男孩走,而后再见面即为陌生人了。《郑笺》之释,符于人情,不仅使读者更清楚女孩子后悔的原因,而且能在内心产生共鸣。
4.朋友
《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笺》:“己留彼去,故随而思之耳。”
5.其它
如由于自己的遭遇:
《邶风·柏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笺》:“言己德备而不遇,所以愠也。”
又如由于恶人的伤害:
《邶风·终风》:“中心是悼。”《笺》:“悼者,伤其如是,然而己不能得而止之。”
(三)揭示心理例即通过揭示心理活动而将情感体现出来。此例与以上第一例不同之处在于并不是直接点明情感,而是通过揭示心理活动体现出情感来的;与第二例不同之处在于诗句中不一定明确说明诗人的情感,《郑笺》通过揭示心理的方式使诗人的情感得以显露。
此例与上两例相比数量明显少很多,主要是与男女爱情相关的,如:
《郑风·东门之墠》:“其室则迩,其人甚远。”《笺》:“其室则近,谓所欲奔男之家。望其来迎己而不来,则为远。”
远与近都是内心的感觉,为什么对方家很近,但却感到人很遥远呢?《郑笺》对女孩子的内心感受加以揭示:“望其来迎己而不来,则为远。”是即所谓“咫尺天涯”,非常符合在恋爱情况下的感受。可见《郑笺》对于人情的把握还是非常深刻的,通过将女孩子内心曲折幽微的想法阐释出,使读者产生共鸣,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郑风·溱洧》:“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吁且乐。”《笺》:“女情急,故劝男使往观于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宽大又乐也。于是男则往也。”
《郑笺》中“女情急”一句,揭示出了女孩子非常想与男孩子一同前往洧水嬉戏的心理,一方面显出女孩子的活泼可爱,另一方面还表现出女孩子对这男孩子的挚爱,惟恐失去,所以一定想邀请男子一同往观,情真意切,令人不由得会心而乐。
《陈风·月出》:“劳心悄兮。”《笺》:“思而不见则忧。”
《郑笺》通过“思而不见则忧”,揭示出男孩“悄兮”的心理原因,说明男孩对女孩的深深的相思与爱慕。
又如与夫妻相关的:
《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笺》:“心曲,心之委曲也。忧则心乱也。”
《疏》:“今乃远在其西戎板屋之中,终我思而不得见之,乱我心中委曲之事也。”妻子因丈夫远征在外,心中烦乱。《郑笺》一句“忧则心乱也”,通过揭示妻子的心理,不仅说明了妻子内心烦乱的原因,而且点明妻子对丈夫的忧心,体现出妻子对丈夫浓浓的爱与关怀。
又有与君臣相关的,如:
《卫风·硕人》:“大夫夙退,无使君劳。”《笺》:“庄姜始来时,卫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无使君之劳倦者,以君夫人新为妃耦,宜亲亲之故也。”
从此句诗中可见大夫们担心国君过于劳苦,对国君无比关心。为什么呢?《郑笺》中解释了:“以君夫人新为妃耦,宜亲亲之故也。”为了国君退朝后能与燕尔新婚之夫人相亲爱,故不能在朝堂上过于劳累。由《郑笺》之阐发,尤可见大夫们对国君考虑之周到与体贴。大夫们对于国君之关心,在《郑笺》的阐发下显得更为生动形象了。
总之,《郑笺》通过揭示诗人的心理,使诗人掩藏在诗句下的真情实感得以显露,使之可触可感,从而令读者易于领会。
(四)释常情例所谓常情,即人类普遍的道德、思想、感受,通过对这些加以阐释,烘托或反衬诗中的情感。
烘托诗中情感
《卫风·氓》:“不见复关,泣涕涟涟。”《笺》:“用心专者怨必深。”
女子不见男子到来,内心悲苦,泣涕涟涟。《郑笺》此句“用心专者怨必深”——所谓情愈切则怨愈深,可谓道破古今人之常情。《郑笺》通过说明人类这一普通的感受,将女子内心之悲怨烘托地更加突出与明显。
《唐风·葛生》:“夏之日,冬之夜。”《笺》:“思者于昼夜之长时尤甚,故极之以尽情。”
夏天白昼最长,冬天夜晚最长。我们都有同样的感受,在夏日与冬夜之时,往往会生出对亲友深切的思念之情。《郑笺》通过说明人类这一普遍的感受,将诗中妻子对亡夫的思念之情烘托地更加深切,并且亦使读者产生类似的感受,从而与诗中之情相互共鸣。
2.反衬诗中情感
《小雅·小弁》:“民莫不谷,我独于罹。”《笺》:“天下之人无不父子相养者,我大子独不然,日以忧也。”
父亲对于儿子有养育之责,这是人之大伦,也是人类最自然的情感。《郑笺》通过点明这一普遍的人类的情感,对比反衬出太子不得父王养育时的痛苦与悲伤。
《周南·螽斯》:“螽斯羽,诜诜兮。”《笺》:“凡物有阴阳情欲者无不妬忌。维蚣蝑不耳,各得受气而生子,故能诜诜然众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则宜然。”
配偶之间是排它性的,动物如此,人类亦然。郑《笺》此语言物性人性之相通,反衬出后妃之不嫉,使嫔妾皆得进御,而使王之子孙众多。
(五)释名物例即对名物的解释。这里对名物的解释与《郑笺》一般的对名物的训诂不同,并非对名物加以定义,而是针对诗中之情而对名物加以有所侧重的解释,以烘托或反衬诗中的情感。
如对情感烘托者:
《豳风·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笺》:“此五物者,家无人则然,令人感思。”
《传》:“果臝,栝楼也。伊威,委黍也。蟏蛸,长踦也。町畽,鹿迹也。熠耀,磷也,磷,萤火也。”《毛传》中对诗中提到的五种事物都加以了解释,《郑笺》却未再如《毛传》一样从训诂上解释,反而说明了这五种事物的一个特点,即都是家无人的时候才有的,由此可见这位征士离家时间之长,并可见且征士的家人俱已下世,于是由此烘托出场景的荒凉、凄清,衬托出征士归家时看到这一番场景时内心的伤感与孤寂。
如对情感反衬者:
《小雅·采绿》:“终朝采绿,不盈一匊。”《笺》:“绿,王刍也,易得之菜也。终朝采之而不满手,怨旷之深,忧思不专于事。”
《郑笺》通过解释绿(即王刍)的特性——易采得,反衬出妇人采了一早上却没采满一手之慢,说明此妇人心不在于采绿而在忧心在外的丈夫,以体现出妇人对丈夫的担心与爱。
(六)释礼例即通过对礼加以阐释,以突出诗中的情感。如:
《邶风·燕燕》:“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笺》:“妇人之礼,送迎不出门。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己愤,尽己情。”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君子曰,非礼也。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踰阈。”可见依照礼仪,妇人送迎都不能出家门。现在庄姜送戴妫归国,不仅出家门,而且远送至郊外,由此衬托出庄姜对戴妫的深谊,以及对州吁胡作非为的极端不满。
《小雅·采绿》:“予发曲局,薄言归沐。”《笺》:“礼,妇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发,忧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将归者,我则沐以待之。”
《郑笺》认为依礼,妇人在夫家时,应将头发簪起来。可是这位女子却散乱着头发,一可见该女子内心忧伤,无心梳妆;二则女为悦己者容,悦己者不在,则不必容,待丈夫归时方再沐髪而容。由此衬托出丈夫行役在外女子内心深深的思念与感伤之情。
(七)释喻例即说明诗句中用喻之处,以突显其中蕴含的感情,如:
《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笺》:“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复出。犹我言伯且来伯且来,则复不来。”
《郑笺》说明这句诗以人们希望下雨而日出,以喻自己希望丈夫回来却屡屡落空,以体现妇人对丈夫的思念,对丈夫归来的盼望,对国家用兵日久的不满。
《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笺》:“蒲以喻所说男之性,荷以喻所说女之容体也。”
《郑笺》说明这句诗以蒲喻男孩的体性滑利,以荷喻女孩的容貌漂亮,亭亭玉立,以见此男孩与女孩的相互喜爱与欣赏之情。
《郑笺》将《毛传》认为是“兴”的诗句都解作作比喻[⑩],相关的条目非常多,故这里仅约举二则,以示其例。
(八)释写法例《郑笺》有时亦说明诗句中之写法,以体现诗中之情。
如释凡例:
《豳风·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笺》:“凡先着此四句者,皆为序归士之情。”
如释再言:
《小雅·四牡》:“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笺》:“人之思恒思亲者,再言将母,亦其情也。”
《四牡》这首诗,前面有一句“不遑将母”,而这句里又出现了一次“将母”。《郑笺》对这种写法加以解释,说明这是诗人思亲情所致,以体现诗人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如释重言:
《商颂·烈祖》:“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锡无疆,及尔斯所,既载清酤,赉我思成。”《笺》:“重言嗟嗟,美叹之深。”
所谓“重言”,即一字或一词在一句中重复二次。《郑笺》通过解释这首诗中“嗟嗟”之重言,说明诗人对于烈祖的赞叹,体现诗人对于烈祖极度的赞美与爱戴。
三、《郑笺》阐发情感的特点从以上对《郑笺》阐发诗中情感方法的论述中,我们可见《郑笺》阐发情感时的以下三个特点。
(一)从阐发的方式上看,《郑笺》中有大量的对诗中情感的直接点明,亦有部分对诗中情感细致入微的阐发。第一,从以上论述可见,《郑笺》中有大量对诗中情感直接点明的文字,主要为“直接点明诗中情感例”。通过这种方式,《郑笺》将诗中情感直接突显出来,使读者得以立刻领会。
第二,亦有部分对诗中情感细致入微的阐发。主要为“释因例”至“释喻例”。综而论之,这类阐发有以下三大作用:
将诗中情感具体化、清晰化,令人可感可触。
情感虚无缥缈、难以捉摸。要对其加以阐发,首先就要将虚的情感坐于实处,从而使读者能够把握理解。如说明原因,以见诗人产生此情此感的前因后果;或揭示诗人心理,见诗人产生此情此感的心理机制,均可将情感化虚为实,从而得以领会。主要见于上文的“释因例”与“揭示心理例”两则。
2.消除与诗人时代之隔阂,自然领会诗中之情。
有时我们对诗情的不理解,其实是由于时代隔阂,于名物、典章、礼法、譬况等不熟所致。若将其解释清楚,诗中所要表达之感情自然豁然明了。主要见于上文的“释名物例”、“释礼例”、“释喻例”三则。
3.使诗中所要表达的情感与我们的日常体验或人类普遍的经验相符,从而令读者于诗情更易领会,并产生共鸣。
如果说上两种作用的本质是“我去就情”的话,那么这一作用就可称为“情来就我”,即将诗中的情感化为每一个人都有的经验与体会,使读者能从自己的体验中切身感受到诗中所要表达的情感。主要见于上文的“释常情例”。
另外,《郑笺》中亦有少数对诗中写法的说明。但《郑笺》并未对《诗经》之写法加以系统考察,亦未形成通例性的认识。所以这不是十分重要的特点。
(二)从内容上看,《郑笺》对诗中情感的阐发都还是依从于诗序的,但在部分阐发中已可见脱离诗序的端倪。《郑笺》在阐发的诗中的情感时,大部分都是与诗序相合的[?]。但在一些诗中,已可见逐渐脱离诗序政教说的端倪,尤其与《毛传》相比则显得尤为明显。
如《齐风·鸡鸣》:“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笺》:“虫飞薨薨,东方且明之时,我犹乐与子卧而同梦,言亲爱之无已。”《诗序》:“《鸡鸣》,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毛传》解释这句为:“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与《郑笺》相比,《毛传》更遵从于诗序,完全是从政教上加以理解的。可《郑笺》却说“言亲爱之无已”也,转着眼于夫人与国君间的亲爱之情,这已与诗序政教的传统不同了。
又如《陈风?泽陂》:“有美一人,伤如之何!”《笺》:“伤,思也。我思此美人,当如之何而得见之。”《诗序》:“《泽陂》,刺时也。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可见是对男女淫泆的批评。《毛传》对这句诗的解释为“伤无礼也”,即诗中的“伤如之何”,乃诗人对不守礼的女子的感伤。此女尽管美好,但不能守礼,是故君子见而感伤之。很明显,《毛传》中之诗人(君子)是以一局外人的姿态看待诗中事件,并从一礼法的角度加以评论。而《郑笺》却认为是诗人在与心上人分别后的感伤。所悦之女思之而不能见,故甚为忧思。是故《郑笺》中之诗人是思念女子的男子,此诗句即表达了男子自己对女子深深的喜爱和思念之情。由此可见,此诗中《毛传》之说显得拘礼而板滞,有很浓重的教化意味,与诗序是相合的。而《郑笺》之说则动情而感人,体现出爱情的迸发和情感的涌动。尽管孔疏在申郑时,最后仍不忘说一句“刺时也”,似乎《郑笺》认为诗句是通过描写不好的行为以讽刺此行为。但不论如何,单独看笺已看不出讽刺之意,而完全是男子与女子情感的表露。在某种程度上,《郑笺》在解释这句诗时已对诗序有了一定的破除。
又如《郑风?东门之墠》:“其室则迩,其人甚远!”《笺》:“其室则近,谓所欲奔男之家。望其来迎己而不来,则为远。”《诗序》:“《东门之墠》,刺乱也。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也。”即对男女不待礼而奔的批评。《毛传》:“迩,近也。得礼则近,不得礼则远。”这还是从礼法的角度出发的。《郑笺》却详述女子心理:男子之家并不远,但女子因为觉得对方不来见己,故而在心理上感觉非常的遥远。由此可见,《郑笺》中远与不远完全由女子心中的感觉所决定,郑在解释诗句时是完全从情感的角度出发的。与《毛传》相比,《郑笺》此处说诗已将情感置于礼上,不再从礼的角度对诗中之事加以评判,转而沿着人之常情对诗中人物加以理解,对其情加以阐发。再如此诗末句:“岂不尔思?子不我即!”《笺》:“我岂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亦可见《郑笺》完全是从情感的角度阐释诗句,而丝毫看不出诗序所谓的“刺乱”的痕迹了。
由此可见,《郑笺》在对部分诗歌情感的阐发中,已经有脱离诗序的情况出现了。但是,这些还只是“端倪”而已,并非普遍的情况。因为从数量上看,《郑笺》的这些阐发还非常少,远远比不上对诗序的遵从。从内容上看,即便在以上所举诸诗中,《郑笺》对其它诗句的阐释还是在诗序的框架之下进行的,从一首诗的整体来看,并未抛开诗序。
总之,《郑笺》对诗经情感的阐发大部分都是依据诗序而作出的,也有少部分对诗序有所脱离。但这些脱离为数还非常有限,仅是端倪而已。
(三)从效果上看,《郑笺》对诗中部分情感的阐发简练、准确而深刻,乃至成为人们共通的情感的代表词句。主要见于上文的“释常情例”中,其它例中也略有一些。依《郑笺》所阐发情感的类型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男女之情
《卫风·氓》:“不见复关,泣涕涟涟。”《笺》:“用心专者怨必深。”
郑笺此语,可堪称作妙言警句了。其实我们都有体验,当一人无比在意、无比钟情于另一人时,自然无时无刻不情系于之。而对方若稍有不合己意之举,那怨恨自然也会无比之深。郑笺此语,可谓是以高度浓缩的表达洞彻人类普遍之情。
《陈风·月出》:“劳心悄兮。”《笺》:“思而不见则忧。”
思念一美丽女子而不见其人,故内心忧闷。相思时切切期盼之情,盼而不见之忧心,正是如此。
2.夫妻之情
《周南?螽斯》:“螽斯羽,诜诜兮。”《笺》:“凡物有阴阳情欲者无不妬忌。维蚣蝑不耳,各得受气而生子,故能诜诜然众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则宜然。”
所谓“凡物有阴阳情欲者无不妒忌”,乃言人性物性之相通,读之令人哑然失笑,却又不得不点头称是。人于配偶之独占与排它,岂非如是乎!
《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笺》:“心曲,心之委曲也。忧则心乱也。”
丈夫在外打仗,妻子忧虑之而致心乱。担心思念亲人之亟,亦正如是。
总之,《郑笺》对以上诗中情感的阐发,不是长篇大论,而是用短短的几个字点明人类的普遍情感。由于这些阐发简练浓缩而又意蕴丰富,甚至已成为人们普遍情感的代表词句。由此可见,一方面郑玄对于诗中的情感有非常好的洞悉与把握,另一方面郑玄本人或即是对情感非常通晓之人。
四、前人谓《郑笺》“按迹以求性情”所举例证驳证以上从正面说明郑氏于诗中之情其实是有着非常深刻的感受与充分的阐释的。下面则从反面对前人论《郑笺》“按迹以求性情”所举之例证加以分析论述,以见前人所谓“按迹以求性情”之失实。
从前引李清臣诸人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说《郑笺》“按迹以求性情”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诗是源于内在思想情感的,礼则是外在的行为表现。
第二,郑玄以礼来训解诗,就是从外在的行为表现来说明内在的思想情感。
第三,由于以上第二点原因,导致了《郑笺》的“繁塞而多失”。
关于《郑笺》是不是“繁塞而多失”,本文暂不讨论,但至少由此可以看出李清臣对郑笺的“以礼训诗”持的主要是否定的态度。其实,诗与礼之间的关系是需要具体讨论的,并不能简单地说以礼解诗好还是不好。首先,郑玄所据之三《礼》,其所反映之时代本身就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后儒对先前社会的想象。所以,若《郑笺》所据之礼的确与诗之内容相合,那么郑玄以礼笺诗即是合理的,有助于我们对诗的理解,如上文中的“释礼例”;反之则不合理,对于我们理解诗意也会造成妨害。其次,诗的主旨到底是什么,也是有待讨论的。从今天看来,《诗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阐发诗人思想感情的诗篇,如关于爱情、友情、亲情诸诗。但还有一部分诗很难说是对某种思想感情的阐发,如《大雅》和《颂》中的史诗和祭祀诗,这些与某种特定的思想感情并无太大的关联。所以,对于祭祀诗从礼的角度加以阐释和理解,正是很合适的,如对《清庙》、《维天之命》诸诗的笺释;而对于阐发情感的诗,一味地也从礼的角度加以阐释和理解,就必定与诗意相背了。总之,关于以礼训诗到底好还是不好,亦需要分情况加以讨论,不能一概论之。
若考察李氏举例,可以发现,诸例间其实各有参差。《狼跋》一诗,李氏曰:“状周公安闲自得于谗疑之中,故有‘公孙硕肤,赤舄几几’之句,而郑谓之公逊。”可是郑玄将“公孙”解为“公逊”,看不出丝毫引礼相释之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转引这句话时即将此例去掉,可见其亦不认为此例属“以礼训诗”。《思齐》一诗中,郑玄将“不谏亦入”理解为入于宗庙,其实是受前一章中“雝雝在宫,肃肃在庙”的影响。郑玄将“肃肃在庙”理解为“(群臣)祭于庙则尚敬”,故在下章中解“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时就会说“文王之祀于宗庙,有仁义之行而不闻达者,亦用之助祭”,可见这是前后相承的。《正义》在疏解“雝雝在宫,肃肃在庙”所在之章时亦说:“郑以为此与下章连。”可见郑玄将“不谏亦入”理解为入于宗庙,与其说是以礼解诗造成的,不如说是对诗篇章间的关系理解不同造成的。《庭燎》一诗,“郑玄以为设鸡人之官”,其实是为了阐发诗序而作出的解释。此诗《小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郑笺》:“因以箴者,王有鸡人之官,凡国事为期,则告之以时。王不正其官,而问夜早晚。”可见是为解诗序而说的。其实此序中“因以箴之”,到底箴的是宣王的什么,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毛诗后笺》引翁氏语云:“笺释箴义谓不正鸡人之官固非,而后来诸家求其说而不得。”[?]余冠英《诗经选》中对于此诗之旨亦只说:“这是写周王朝会的诗。”[?]可见“因以箴之”一句实难理解,《郑笺》也只是为寻一较合理的解释而已,所以严格地说也不能算为以礼训诗之误例。至于《绿衣》一诗,《郑笺》从《周礼》而改“绿”为“褖”,确系其误,这乃是郑玄之“前见”中以为《诗》中篇篇有礼所致[?]。
总之,对于李清臣及后来诸人之语,其指出《郑笺》存在对礼过度阐释的现象,这是有道理的。但其对《郑笺》以礼训诗的方法全面加以否定,则是不恰当的。其所举之例中,严格来说真正称得上是以礼训诗而致误的,惟有《绿衣》一首。
那么对于《郑笺》存在的一些对礼过度阐释的倾向,应该如何理解呢?我认为,首先,“以礼训诗”是当时训释《诗经》的普遍情况。不唯郑玄如此,前人皆然,如《毛传》和三家《诗》等。因而郑氏以礼笺诗,只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而后代复有大量学者如此,乃历代学者之通病,不应专门苛求。其次,“以礼训诗”是用政教说经的必然结果。汉人说《诗》皆从政教的角度出发,郑玄亦只是遵从这一传统而已,不必专作批评。再次,“以礼训诗”亦非郑玄训释《诗经》的唯一方式。最后,《郑笺》中即便存在以礼过度阐释诗句之处,亦不意味着郑氏于诗情不解。从上文所举诸例中,尤其是对《郑笺》阐发情感特点的第三点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出郑氏于诗中情感是有非常深切的体会的。在某些地方之所以礼过度阐释,亦只是遵从政教说经的方式并继承先儒的传统而已。
五、结语综合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郑笺》对于诗中之情阐发是非常丰富的,或明白显豁,或委曲婉转,或直抒情意,痛快淋漓,或曲中其隐,令人解颐。郑氏之释解,可谓谅人察己,细致入微,曲尽情致,深得风人之旨。而郑玄解诗之语,亦成为名言警语,为后世情感表达与诉说深情的经典词句。与其前之《毛传》相比,可谓戛戛独造,亦启发后人甚大。同时,本文对前人论《郑笺》释诗“按迹以求性情”所举诸例证,也一一进行了析解,认为这些例子各有其合理的解释缘由,从绝大多数例子从中很难得出郑氏“按迹以求性情”的结论。因此,千余年来评价《郑笺》影响颇大的这一说法,并非事实,有失偏颇。
[①][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别集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缩印本,年3月,第册,页。
[②][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清]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年12月,页。又其《汉艺文志考证》亦引之而稍略。(张三夕、杨毅点校,中华书局,年1月,页。)清儒朱彝尊《经义考》中亦略载李清臣语。(《点校补正经义考》,冯晓庭、陈恒嵩、侯美珍点校,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年6月,第3册,页。)
[③][清]胡承珙《毛诗后笺》,郭全芝校点、贺友龄审订,黄山书社,年8月,页。
[④][清]胡培翚《胡培翚集》,黄智明点校、蒋秋华校订,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年11月,页。
[⑤][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附补逸)》卷三二,商务印书馆,年6月,页。
[⑥]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年5月,页。
[⑦]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年。
[⑧]沈薇薇《郑玄〈诗经〉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年。
[⑨]李世萍《郑玄毛诗笺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年1月。
[⑩]杨新勋《论〈《郑笺》〉对〈《毛传》〉“标兴”的认识与发展》,《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年02期,页-页。
[?]关于《郑笺》阐释诗情大部分与《小序》相合的情况,详可见山东大学孔德凌博士论文《郑玄〈诗经〉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年)的第四章《郑〈笺〉与〈毛诗序〉》,兹不再赘述。
[?]《毛诗后笺》,页。
[?]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年10月,页。
[?]梁锡锋《郑玄以礼笺诗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年,页。
[?]《郑玄以礼笺诗研究》,页24。
作者介绍:李林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文章出处:本文原刊於《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三辑)
感谢李林芳博士授权学衡转刊。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欢迎与朋友分享!阅读更多原创文章,请在北京治疗白癜风哪个医院最好到哪家白癜风治疗好
转载请注明:http://www.sohkw.com/wadwh/3754.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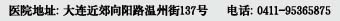
当前时间:
